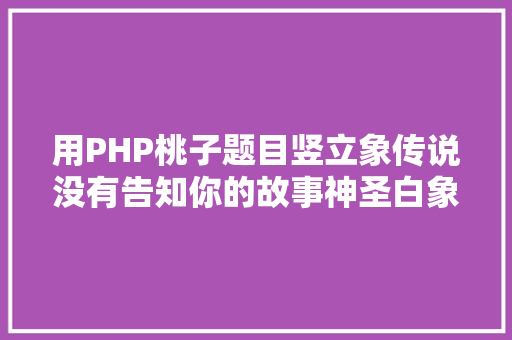动画电影《直立象传说》剧照。
不过,高档级的智力并没能替它们取得和人类平分秋色的地位。在片中,我们的同类不是将它们当成奇珍奇宝,而只是视作可买卖的普通财产和承担体力活的畜生。既然这种动物出色的智商在短视的农场主和牲口贩子眼里除了方便理解命令便毫无用途,那么其丰富的情绪、对平等权利和自由生活的渴望当然也会被主人完备忽略。被人类奴役,是它们不幸的命运。
随着故事深入,不雅观众得知了这群象的历史。它们的先人和人类一样直立行走,但为了阔别人类的恶行,直立象分解成两支:一支向北方无人区迁移,更进化出机动的双手,会采摘树上的果子、吹奏乐器、吸烟斗,乃至生产武器、兴建城市、布局繁芜的社会与政治体系;而留下的一支由于被人类使令劳作(紧张任务是弯腰犁地),代代相继,双手沦为无用之物,直立也逐渐退化,形成屈曲厚实的背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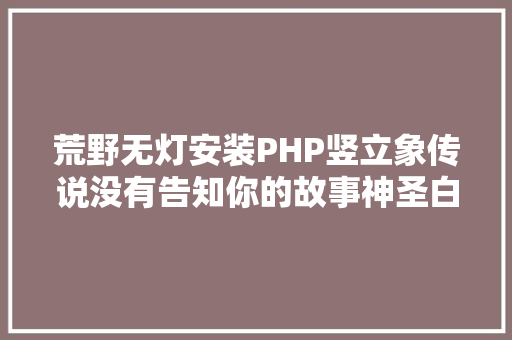
剧情的走向不难猜到。身为这不幸族群的一员,主角木子李(普通话版把Mosley音译成了这个略显尴尬的名字)背负的命运当然是接续远祖的传统,找回直立行走的荣光,永别那世代被奴役的命运。觉醒、出走、受难、进化、反抗,主角的经历在许多我们熟知的史实和故事里都不难找到原型。
一个最易涌现的遐想是,桃栗象是美国南方栽种园黑奴的化身。的确,明明有着普通人一样平常的智力与情绪,却居于奴隶地位,被买卖、奴役和施以暴力,是木子李们和黑人奴隶共同的遭际。
现实中,象的形象与黑人也一度有某种联系。史前期间,象广泛分布于各地。后来,美洲大陆的猛犸象、乳齿象等生物渐次灭绝——贾雷德·戴蒙德在《第三种黑猩猩》中描述了超过白令陆桥进入美洲的猎人们如何在短韶光内将猛犸象赶尽杀绝。象科仅剩两个属,栖息于亚洲和非洲。
《第三种黑猩猩》,[美]贾雷德·戴蒙德著,王道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2月。
在亚洲,印度河与黄河流域的先民们驯服野生象,用作战象。多年后,波斯帝国通过从印度获取的15头战象极大地威慑了亚历山大大帝,这很可能是欧洲人第一次感想熏染象的巨大体型带来的震荡。只管此后直到中世纪,欧洲断断续续有利用战象的记载,但15世纪后火器遍及,象的上风荡然无存,也就不再被欧洲人用于战役。
军事用场之外,象曾是欧洲国家外交时极为宝贵的礼物,普通人则无从得见。直到文艺复兴期间,象的形象仍常常涌如今欧洲的绘画、雕塑、手工艺作品中,象征力量与聪慧,但有些形象实在不怎么惟妙惟肖,想必作者也没有亲眼见识过这远方的珍物。此后,在经历了从启蒙运动到生物进化论洗礼的欧洲人眼里,象逐渐退去了神秘光环。
另一方面,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殖民奇迹风起云涌。原来已于非洲存在数百年的奴隶贸易变本加厉,大量奴隶被贩往美洲。时日既久,奴隶制度的存废逐渐变成人们关注的焦点。故意思的是,人们对付象的印象也涌现了变革。
白象引发美国焦虑
由肤色引发的种族焦虑
1884年,马戏团经营者巴纳姆花了巨大努力和高昂用度,将白象“通达隆”从缅甸国王手里买下,先后运到英国和美国巡展。这是两国"大众年夜众第一次见到白象,《纽约时报》的文章描述了通达隆的外面:“额头有一大片粉红的色块,蔓延过它的眼睛和半根鼻子。耳朵呈奇特的三角形,边缘同样是肉色的粉红,还有大片斑驳的斑点,胸部和肩膀也有斑点。躯干下面也是肉色的。”多伦多OCAD大学英语系教授罗斯·布伦指出,肉色是个暧昧的用词,由于它隐约指向的是白人的肉体。
几年后通达隆去世于失火,巴纳姆在回顾文章中承认自己初见它时有些失落望,由于那种白不是纯白,而是患白化病导致的斑点与色块。“天下上没有真正纯白的象,那种神圣的、技能性的、上帝所创的白。”
但在1884年,不明就里的"大众仍对通达隆好奇与着迷,引发了一场颜色风波。旅行作家小弗兰克·文森特早前写过著名游记《白象之地:东南亚的风景名胜》,此番他则在题为《白象》的文章中指出:“白象只有在明显的玄色的比拟下才是白色。混血儿不完备是白人,但与纯血统的黑人比较,混血儿便是白人。”就在不到二十年前,南北战役结束,《宪法第十三号改动案》颁布,正式在全美废除奴隶制度,但遗留的种族问题远未办理。文森特的文章比《纽约时报》那篇锐利得多,它明确地将白象和种族问题挂了钩,并谈论了白度的问题。
记录片《大象》剧照。
同样在1884年,还有两头白象在美国展出,分别是巴纳姆自己的“蒂普”和福里鲍的“亚洲之光”。它们实在都是普通的象(文森特将普通象称为“黑象”),只是被奸商主人用油漆反复涂成了白色,以是看起来反而比通达隆更白。但巴纳姆和福里鲍的阵营交相攻讦,指称对方的象(包括通达隆)是被涂白的冒牌货。
“白象之争”一度闹得不可开交,引发了一场被历史与动物学者莎拉·阿马托称为“关于白人、种族、种族纯洁、种族优生和白人特权”的大辩论。比如,有人对传说中巴纳姆和福里鲍用来为象着色的技能十分焦虑,担心它会重塑白人和黑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纽约时报》一篇题为《一个有趣的实验》的文章讽刺性地假想了如了局景:“它若成功被推广,有色人种在我们中将像神圣的白象般罕有……漂白的埃塞俄比亚人白得刺目耀眼,堪与雪相媲美。麦迪逊大街上最纯洁的金发女郎在汤普森街的美女身边显得黝黑,曾经的白人溘然变成有色人种。白人的肤色被漂白的有色人种唾弃,这是种奇怪的觉得。所有仍旧存在的针对有色人种的法律法规将适用于高加索人种。我们将不得不通过一项新的民权法案,以确保自己能进入酒店和卧铺车。如果漂白的有色人种屈尊采取白人的表达办法,我们乃至可能会听到自己被歧视地叫成‘黑鬼’。”
1884年的白象之争。
同年晚些时候,两则肥皂广告再为白象之争推波助澜。广告一描述了一头象和它皮肤黝黑的驯兽师,后者一手握着肥皂,一手用布擦洗象的皮肤,将它的玄色洗白。广告二则是白人男孩给黑人男孩沐浴:第一幅图中,黑人男孩坐在浴缸里,白人男孩拿着肥皂站在他身边;第二幅图中,黑人男孩坐在浴缸外,脸部仍是玄色,但身体的别的部分已经变白。
上述文章和广告隐含的逻辑是,象和人类肤色的白度都是可变值,能被商品调节。如果肤色不是绝对的,由肤色引发的种族问题就显然是一种社会建构。布伦不失落深刻地指出,这个结论大概会令种族主义者大惊失落色,但他们也可以反过来推论出,白人必须通过严格掌握白度来维系自身的特权,以免有色人种有朝一日篡夺了他们的好处。
杀人玛丽遭人杀
象与黑人是如何被混为一谈的
人类的先祖走出非洲,足迹遍布各大陆,蜕变出浩瀚文明。讽刺的是,留在非洲的那一支的后裔里不少人后来沦为奴隶。木子李和它的同类们险些照搬地演绎了这段历史,不过《直立象传说》用生理退化造成的恶性循环来阐明这一悲剧,这只是文艺作品的适度想象,在现实中彷佛没有对应的例子。
文明间进步与掉队的客不雅观差异并非人种利害造成。对此,戴蒙德在他的另一部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已经不厌其烦地反复论证过:“欧洲在非洲的殖民并不像某些白人种族主义者以是为的那样与欧洲民族和非洲民族本身之间的差异有关。正好相反,这是由于地理学和生物地理学的有时成分所致——特殊是由于这两个大陆之间不同的面积、不同的轴线方向和不同的动植物品种所致。”不过,他在这本书中提醒读者,“日本谢绝枪支和中国抛弃远洋船只(以及抛弃机器钟和水力驱动纺纱机),是历史上伶仃或半伶仃社会技能倒退的著名例子。”若将桃栗象从直立重回匍匐理解成对此类文明倒退事宜的一种隐喻,它们的悲剧不失落为一记洪亮的警钟。
如果把标准放宽一些,我们还会看到现实中的象和黑人经历了更多相似的事情。1916年,斯帕克斯兄弟马戏团一头二十多岁的母象“玛丽”被当众处以绞刑,由于它在众目睽睽之下杀去世了大象管理员——只管杀人缘故原由和细节众说纷纭。秉性温和的玛丽很快规复了镇静,围不雅观群众却怨怒不已,高呼要杀去世它。有人当场对它发射了五枪,但不管用。为了回应这份激愤,马戏团老板决定对玛丽公开处刑。在超过2500人的见证下,玛丽被吊去世——第一次,链条断了,一万多磅的玛丽重重摔在地上,髋部骨折;第二次,它才断气。
只管当时被蔑称为“杀人玛丽”,但很多年后,越来越多的小说、歌曲和话剧讲述了玛丽的遭遇,大多抱以深切的同情。作家琼·范诺斯达尔·施罗德也是对玛丽故事感兴趣的人之一,她在作品中引述了托马斯·伯顿的文章,后者于1971年揭橥在《田纳西民俗学会公报》上——那正是黑公民权运动摘取阶段性成果的岁月。
施罗德略施笔墨,勾勒出玛丽和黑人这两者在社会心理层面潜在的关联:“伯顿写道,一些当地居民回顾起‘两个黑鬼喂养员’被绞去世在玛丽阁下,还有人回顾起玛丽的尸体被烧去世在一堆十字架上。‘这种信念,’伯顿写道,‘可能是由于绞刑与发生在欧文镇的另一事宜的领悟,即一名据称绑架了一名白人女孩的黑鬼被烧去世在一堆十字架上。’杀象:奇不雅观。杀‘黑鬼’:另一种奇不雅观。那是1916年——对美国的替罪羊来说是个好年头。”
南北战役结束、奴隶制度废除数十年后,仍有许多黑人在私刑中被杀害。伯顿钩沉史实,弦外之音;而施罗德将这弦外之音提要挈领。象和黑人,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群体由于附近的出身与肤色而经历了相似的命运,乃至在白人的影象、想象与潜意识中竟混为一谈。
猎象步枪与《射象》
从野蛮地皮的害兽到未开化的有色人种
除黑人外,工具的印象也投射在其他少数族裔身上。不妨看一看电子游戏,《荒野大镖客2》的故事发生在从1899年到20世纪初的美国,南北战役中伤残的英雄士兵此时已沦为街头行乞的老者。在这个以考据严谨著称、细致刻画了美国上百种鸟兽的游戏的线上版本里,象没有以活物的形式涌现,除了猛犸象的遗骸,游戏中唯一能找到和象干系的元素是一种叫猎象步枪的武器。通过对它的先容,我们得知时人将象看作一种“致命的讨厌害兽”,除了象牙便一无是处:“它们成长于印度和非洲的野蛮地皮,渗出出荒谬的巨量粪便,踏平和花费庄稼而不顾受饿的人们,并且会毫无情由地惶恐,几秒钟之内就把整整一个家庭踩去世,危险度愈甚犀牛或狮子。”
游戏《荒野大镖客2》海报。
此类印象很难说是公允的,字里行间表示了对他者深藏的偏见与焦虑。早在1862年,法国博物学家亨利·穆奥的遗著《暹罗柬埔寨老挝诸王国旅行记》就向西方天下先容了他重新创造的吴哥古迹,从而将东南亚文化引到了聚光灯下。但一头站在19世纪尽头的象仍不会被西方公众年夜众真正接管,管它是非洲象还是亚洲象,反正都是些深色、野蛮、不可理喻、与文明社会为敌的生物。正如在那些人的印象中,缅甸的缅族人、非洲的班图人和新西兰的毛利人的差异很可能没有人类学意义上的大,实质上来说,这些有色人种都是作为白人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一样。
这种成见在20世纪的许多年里仍没有变革。前述玛丽的故事令人想起乔治·奥威尔的《射象》,这是一篇回顾性子的散文。也便是说,文中详载的射杀大象事宜是奥威尔1920年代在缅甸任职时亲手完成的。那么,为什么奥威尔又自称此事让他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真正实质”呢?
那头发情的象和玛丽一样杀了人。去世者是印度苦力,象主人也是印度人。不知是奥威尔太幸运,还是他的对手比玛丽弱得多,我们未来的文豪、此时的射象新手只开了三枪,就杀去世了那头冒失的象。“年纪大的(欧洲)人说我做的对,年纪轻的人说为了踩去世一个苦力而开枪打去世一头象太不像话了,由于象比科林吉苦力值钱。我事后心中暗喜,那个苦力去世得好,使我可以明正言顺地射去世那头象,在法律上处于精确地位。”奥威尔在文末语带讽刺地说。
缅甸当时是英属印度的领土,是根植于殖民主义秩序的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更是迢遥、陌生、未全开化的大陆。在这片地皮上,种族的对立与冲突十分尖锐。此处发生的事情,既是两次天下大战间环球景不雅观的一幅微缩影像,也是许多绵延至今的乱流的预演。回顾象在近几个世纪的遭遇,本日全天下的人们更应该汲取教训,时时警觉,杜绝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奴役、犯罪和伤害,令“桃栗象”们的悲剧不再重现。
参考资料
https://www.elephant.se/database2.php?elephant_id=3864
https://publicdomainreview.org/essay/race-and-the-white-elephant-war-of-1884
https://daily.jstor.org/original-white-elephant/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8%B1%A1
https://blueridgecountry.com/archive/favorites/mary-the-elephant/
撰文 | 张哲
编辑 | 王青
校正 |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