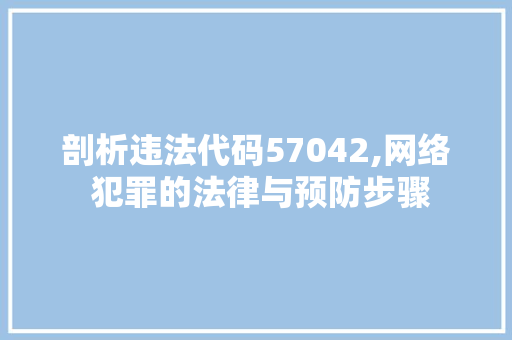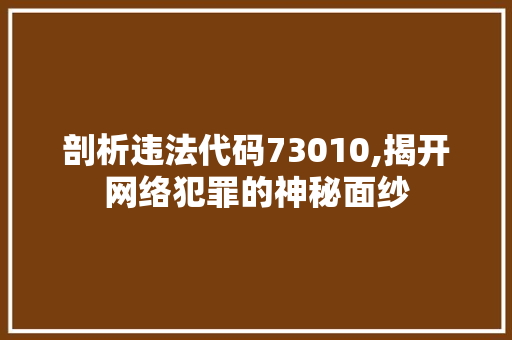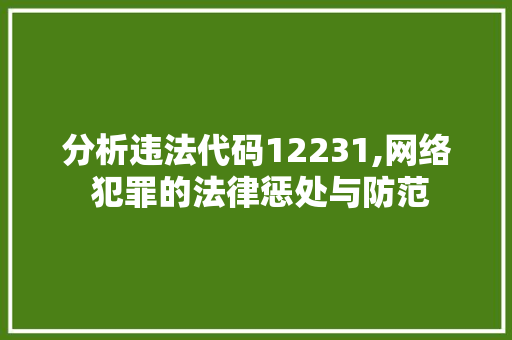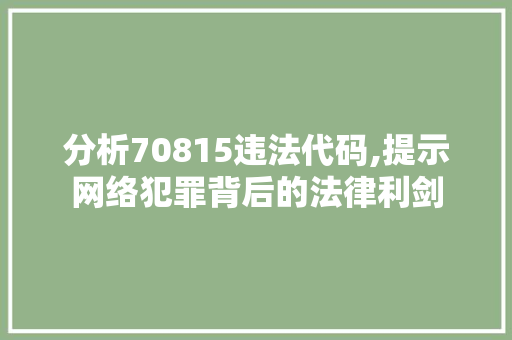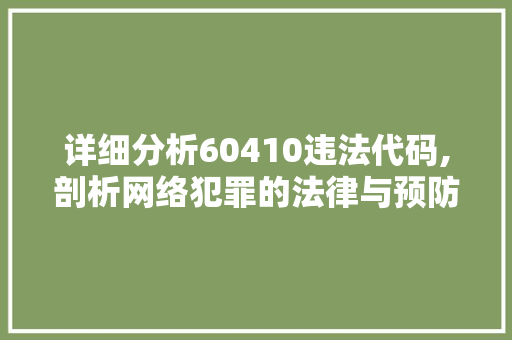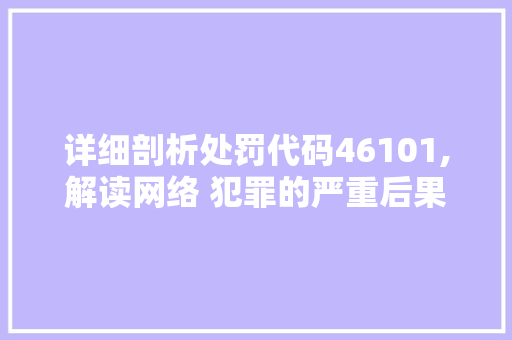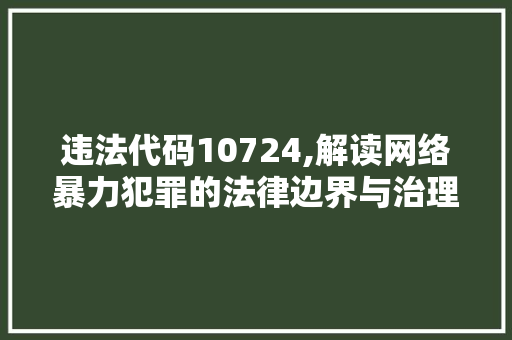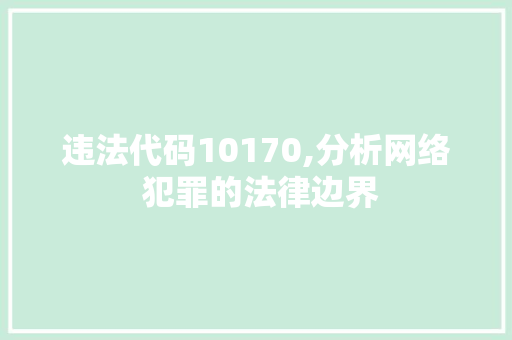近期,金状师打仗了一起诱骗罪案件,当事人及其公司为电信网络诱骗犯罪供应“拉微信群”做事,通过多种手段获取客户微信等干系信息后,组建几十个乃至几百个微信群,再将微信群直接“转让”给他人,变更群主等干系信息,对方终极利用这些微信群进行勾引投资、喊单、网络赌钱、网络诱骗等活动。
这起案件中,由于“拉微信群”确当事人与涉网络勾引投资案件的涉案公司存在诸多事实上的关联性,办案机关现阶段因此诱骗罪进行认定。
现阶段电信网络诱骗犯罪案件的范例特点,是高下游犯罪链条繁芜,紧张表示为前置的推广渠道、技能供应和帮助、做事渠道,以及后续广义上的支付结算、洗钱渠道。由于存在这样的特点,很多关联案件虽然并案处理,或者是由同一办案机关统领,但是再按照传统的诱骗罪理论,直接将该类涉案职员认定为诱骗罪的共犯,以诱骗罪进行定罪、量刑,每每难以做到罪过刑相适应。因此,近年来才会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造孽利用信息网络罪等干系罪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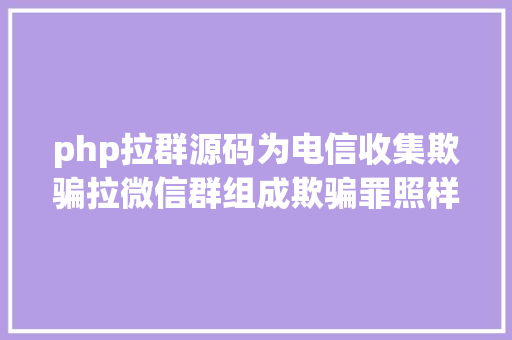
造孽利用信息网络罪的行为模式,包括了“设立用于履行诱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发卖违禁物品、牵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为履行诱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因此,从刑法条文上来看,为电信网络诱骗犯罪活动供应“拉微信群”做事的,应该按照造孽利用信息网络罪认定,其法定刑最高三年,针对绝大多数的电信网络诱骗犯罪而言,该罪名的量刑比诱骗罪从犯的量刑更轻。
但是法律实务中的案件都有其分外性,案件事实也各有不同。同样是为电信网络诱骗犯罪活动“拉微信群”的行为模式,部分案件中行为人是独立的第三方公司涉案职员,与履行诱骗犯罪活动的经营主体之间只是业务上的互助,乃至对方将微信群详细用于何种经营活动都不完备清楚;另一部分案件中,“拉微信群”的乃至是涉电信网络诱骗公司某个部门的员工,抑或两个公司之间本就具有密切的经营关联性、高下游关系,乃至涉案职员除了供应“拉微信群”做事之外,也参与了其他的涉案经营行为。
此时,如果辩方没有谨严审查案件,而是一厢宁愿的认为,由于有更“得当”的轻罪,我们只要大略指出轻罪更适宜本案的定性,办案机关后续当然会变更罪名。此时,控辩双方就可能根本不在同一维度上沟通,结果可想而知。
因此,我们可以说,为电信网络诱骗犯罪活动供应“拉微信群”做事的,一样平常情形下,应该按照造孽利用信息网络罪进行处理。但是,如果一个案件中办案机关认定的罪名是诱骗罪,认为成立诱骗罪共同犯罪,类似于前面当事人咨询金状师的案件,此时我们该当做的,并不是单方面认为办案机关后续一定会改变定性,而是在全面理解案件事实、证据的根本上,厘清办案机关的定罪思路及其依据的案件事实、证据,再进行针对性的辩解,以事实、证据,论证办案机关应该变更罪名的情由。
此外,无论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还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其刑法条文中都有明确解释:“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惩罚较重的规定定罪惩罚”。因此,对付此类案件,完备可能存在重罪风险,乃至是认定多个罪名的情形,须要格外重视。
关于“拉微信群”类涉电信网络诱骗犯罪案件,我们参考一起实务案例,进行辩解磋商:
参考案例:董某某、赵某造孽利用信息网络一审刑事讯断书,(2020)皖0811刑初135号
裁判情由:一、被告人董某某、赵某造孽利用信息网络犯罪事实。2019年2、3月份至案发,被告人董某某、赵某先后应聘至武汉ZC公司分别担当公司卖力人及后勤经理。期间,二人伙同凌某某、谭某某、万某某、刘某某(另案处理)等人在位于XX的公司内履行拉群业务,由被告人董某某、赵某通过电脑软件得到大量手机号码后供应给招募的职员,让招募的职员拨打电话,添加机主,并将故意加入股票群的机主拉入事先准备好的微信群,待拉进微信群机主达到一定人数后,再将微信群转卖给境外诱骗团伙牟利。至案发时,该公司已设立多个微信群。被害人李某某接到该公司职员电话后添加“周某某”微信,被“周某某”拉入“CW互换57群”,后在助理“小夏”、讲师“尤某某”的勾引下安装软件并进行充值投资。
二、被告人周某、杨某、丁某、成某某涉嫌诱骗犯罪事实。2019年9月24日,被害人刘某甲被拉进“擒牛171群”微信群,被告人周某在该微信群内伪装股票讲师“金牌趋势导师”,被告人成某某伪装助理“可可”,被告人杨某、丁某则伪装股民,吹捧讲师,待刘某甲对讲师信赖后,勾引刘某甲与助理、讲师私聊并下载GTS虚拟货币软件APP,后又将被害人刘某甲拉入另一微信群“孔老师先锋体验班25群”连续洗脑,之后由被告人周某诱使刘某甲在该GTS平台进行充值操作购买货币,并在后台掌握货币涨跌让刘某甲亏钱,从而多次骗取刘某甲财物。
三、被告人郝某某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犯罪事实。2018年底,被告人郝某某在做网络直播时与肖某(另案处理)相识。2019年9月份,被告人郝某某明知肖某搭建的GTS货币交易平台是用于履行网络诱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仍应肖某哀求利用肖某供应的源代码在该平台内添加短信验证码、支付模块等系统,并通过微信收取肖某给付的报酬。
本院认为,被告人董某某、赵某设立用于履行违法犯罪活动的通讯群组,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造孽利用信息网络罪且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周某、杨某、丁某、成某某等人以造孽霸占为目的,结伙利用电信网络技能手段骗取他人钱财,并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其行为构成诱骗罪且系共同犯罪;被告人郝晓雨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履行犯罪,仍为他人犯罪供应技能支持,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关于该判例,应把稳以下几点问题:
1.本案中,董某某等涉案职员属于范例第三方做事平台,只供应“拉微信群”做事,在组建微信群后,将微信群转卖给他人,不参与涉电信网络诱骗公司的其他任何经营行为,因此终极按照造孽利用信息网络罪认定。
2.本案中周某等涉案职员在第(二)起案件事实中,涉虚拟货币投资诱骗,其成立诱骗罪的核心事实并非是勾引投资,而是涉案平台存在后台掌握货币涨跌,人为操控也是此类案件中差异造孽经营罪和诱骗罪的核心事实。
3.郝某某等涉案职员在第(三)起案件事实中,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该罪名常常会涌如今电信网络诱骗案件共同犯罪的罪名认定中,技能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类公司及其涉案职员,在特定案件中如果被指控为诱骗犯罪,可考虑以该罪进行轻罪辩解。近年来,由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增设,不少类似案件一审判决为诱骗罪,二审终极改判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量刑大幅降落,该类判例可作为刑事辩解的参考。